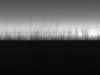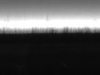任波
我现在意识到,这种幽默与戏谑,与一种严肃的 意图并行,加上一点哀婉,出现在任波一些作品 对绝望的表达中。这一组合默然从事,将观者置 于与物件及其微妙意义相关的一个奇怪位置。由 此,这些作品并不安居于其意义中,也不安居于 我们对它们的经验中,这份不适代表了世上的小 小怀疑。这份微妙也是作品在世上生命的一个重 要部分。它们的呈现,不是好为人师的,也不是 戏剧夸张的。作品的这份“平静”使我们怔住。 它并不以自身表达,它也不要求物质上或智力上 的互动。如果它是一个物件,它站在我们面前; 如果它是一个图像,它被呈现给我们,以供参考。
在追求奇观的赛场上,这份方法上的微妙或许会 被视作其自身最坏的敌人——如果一件艺术作品 并不积极地吸引观众,通常这会被视为一件坏事, 也许显示出些许傲慢、疏离,过于仰仗观者的善意。 然而,这也可以是另一种吸引模式的迹象。
任波的作品并不提供一目了然的意义(换言之, 任波的作品不提供或许可以等同于融入作品能力 的种种解读),虽说这确实是真的,然而,在任 波作品确实吸引人的层面,意味着我们必须再次 思考:一件艺术品在世上何所为,以及我们该如 何应对它(而非艺术品如何应对我们)。这不是 说任波不期待反应,但是,我想,她的作品并不 依赖这么一种反应,而且,或许她游戏的正是反 应的过程,停滞在实现的中段。
任波装置的材料,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可以是现 成品,但是选择与安排,则显露出用心。作品无 题 -14(2011) 创造了一座灯搭建的塔,这些灯是 艺术家经年收集的。无题 -14 使这些灯显得奇怪, 将其从原初的功能中抽离(纵然仍起灯的作用), 以一种新的、未知的形式将它们呈现给我们。看 到这件作品,映入脑际的是承担敬意与回忆之职 的图腾柱。在任波的例子中,这些灯是她在很长 一段时期中收集的物件,并在逐步增加的构成中, 表征那个时期。虽然图腾柱雕刻的形象与形状高度象征人物与事件,至于任波的灯,不费力推出 的解读却是:它是截然缄默的。意义停留在背景 提示,并不将自身强加于对作品的经验或阅读。 连串叠加的灯呈现这一提示,一如消逝不可及的 回声。
“就像没有收件人的信件一样,这些直立的存在 依然漫无目的。既不像选民一样有福,又不像被 诅咒者那般无望,他们充满了无处倾泻的愉悦。” —吉奥乔·阿甘本 2
这里描述的是地狱边缘的居民,尤其是圣托马 斯·阿奎那的地狱边缘。阿甘本将这些死亡灵魂 的不自觉状态,描述为如在婴儿受洗之前已然死 去,于是仍在原罪状态中,却既无补救那一情境 的机会,也无对其状态的责任。所以他们必须“持 续”呆在这个特别的地方,既没有地域“折磨人 的惩罚”,也没有天堂的救赎。这一状态似乎在 其中容纳了太多可能性,而没有实现这些可能性 的机会。我相信,阿甘本此处的意思是:这是一 种自行其道的解放,将注意力从行动目的转向“无 目的的手段”(阿甘本另一著作标题)。
虽然我无法声称自己对阿甘本的著作有任何特殊 洞见,他的思考方式强烈地影响了我的世界观。 我尤其对它应用于艺术行为有兴趣。艺术行为, 是艺术的“进行中”状态,是一种或可潜伏或可 辨识的态势,也是一些艺术家积极利用的一种创 作方法论。我看到,在任波的创作中,传出这种 状态。在地狱边缘中,“进行中”将关注从一个 目的地(例如,天堂或地狱)转开,带入艺术的 语境,即是将关注从一件“完成了的”物件(在 别处我贬义地称之为“无声”或“哑”物件)转开, 朝向通往我们正在观看的点的道路。然而,这个
点并非画廊中平静、稳定的安置状态,而是在途 中的状态。
现在,在很多情况下,任波正生产物件,那这些 物件又如何与我提到的“哑”作品区别?区别部 分地在于意图,部分地在于对物件的经验。任波 的作品,或是生产中着力于过程,或是将着力于 过程视为一种解读方法,她在创作的行动中融入 观众,对纳入的物件,从不持直接的方法。
诸如二十五天的灰 (2008) 这样的作品,或许是任 波作品中过程的最直接表达。纸张满布棉绒,由 粘性滚筒取自她的衣裳,采集了这一基于时间的 剥落。这一进行中的系列成为一份视觉记录,记 录了她的衣服收集而其后又被除去的东西。在这 个例子中,视觉的东西与再现之间有一种奇怪的 关系。这些纸,在某种意义上,比较详细地告诉 我们有关艺术家周遭世界增长的情形。但是,收 集在这里的这些纸构成了一种新花样,仿佛伪档 案,虽非确切,余味无穷。
在任波的作品中,视觉部分或许是主要的,但不 是优先的。例如,她的影像作品,游戏声与光, 也游戏它们的物质本性和屏幕的确切位置。对已 成影像的部分,这些元素于是成了再现性的。任 波能够将影像作品仅仅呈现为一种光源,脉冲调 制的题中之义也是作品潜在意义。经解析的录像 画面,可被视作再现性的,但这些再现图像本身 因顺序的操弄而模糊。无邪碎片 (2006) 展示了一 个扭曲的图像的快版和慢版。两者彼此都不更接 近真相,但分别有一种不同的感受与效果,合在 一起彼此竞争。在白色白光(2012)中,电视机 覆盖于一条裙子、数张塑料纸之下,屏幕被简单 用作光源。
声音似乎是“进行中”的典范。它是被生产 出来的,它被发出,它在录音中旅行,它在 录音中栖居,那些录音总会再度发声,以存 续声音。但每一次发声都是独特的,平行于 一种永在的、模糊的约翰·凯奇式的氛围。 声音本质上是稍纵即逝的,只存在于发声的 时段,每个声音行进到下一个,在分崩离析中, 融入环境中。
拟声的啪嗒啪嗒 (2008) 是一卷直立的塑料 布,一枚悬浮的镭射笔卷入其中,其红色光 点令人眩晕地舞动,同时敲击塑料布,弄出 与标题相仿的声响。它的创作,看似刻意为之, 但是,除了说它“啪嗒-啪嗒”,艺术家最 终必须承认放弃确切定义作品为何的能力。
如果任波的艺术作品有所求,那是别把它们 从世界中剥离出去的安静之求。那些物件并 不果断行事,而是曲折行藏,通过多样的材 料形式与其感官之用,包括四散的抽象声光, 挑战对作品清晰连贯要点的期待。它们以其 材料、光、声,模糊作品彼此的边界,融入 环境。在很多情况下,任波制作物件,或者 构成藏品组的物件(我们离不了这一点), 但这些在模糊化过程中,变得问题重重。它 们对抗着艺术作品有主导性的形式的观念, 对抗着博取关注的观念,对抗着确认艺术家 可辨风格的观念,对抗着可被轻易转入商品 系统的物件(视觉的、声音的,或者其它) 的观念。
于是,可以将这些元素视作某种传送的一部分。没有东西绝对自圆。在这个方向上,那些物件带上 了搅乱其世间在场的一种意义。这不由推理而来,也即 不由外加的意义而来,而是将其自身内在的在场演化为 融入世界的,以此为意义。近似于声音示意的,物件(就 其全部存在)保持模糊,减慢意义的进程。它们表征着 意义的延迟,思考的行动与历时的经验优先,而且,行 动是一种进程,而非完结。
缘于任波作品显而易见的散漫本性,谈论这些作品或许 是困难的,但是,我觉得这接近其欣赏之道。一方面, 每件作品有其特定的吸引力,但很难将这种吸引力视作 通贯其全部作品的一致元素。另一方面,我也指出,她 的作品展示着进行中的存在行为,非关形式,非关象征, 而关乎一种特定的存在方式。这一点,我认为,是任波 作品中一致的元素,并且使观者以新的眼光看待艺术作 品。这样的艺术作品超越,或者并不特别依赖安居于空 间中、扮演艺术作品角色或是保持消费品标准的艺术的 绝对实体。任波的作品安静地拒绝接受那一角色,谈不 上安居,而是打扰着这个客体化、物件化的世界以及紧 随其后产生作品的消费世界。在一些情况下,它们难于 框取为一件东西,或别的东西,打搅着这个物件的世界。 当然,它们也打搅着艺术的世界:它们不愿意安分地适 应现有艺术体制,创造出关于如何在艺术的社会环境中 处理这类物件的问题,甚至,更进一步,动摇艺术作品 为何、艺术作品何为的观念。
| 分享: |